点击上方“辽大民俗学”可订阅哦!
内蒙鄂尔多斯的朝格日布与辽宁喀喇沁左翼的武德胜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蒙古族故事家。虽然这两位故事家已离开我们多年,但因他们的故事均采录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时我国各地民间讲故事的“语境”还未受到现代化的明显冲击,故而两位故事家留传下来的众多精美且几近“原生态”的蒙古族民间故事,在今天已似陈年的老酒,虽岁月弥久却愈发甘冽醇香。尤其在当下,重新审视评估两位蒙古族故事家留下的这笔民间文化遗产,其价值更是难以估量,弥足珍贵。众所周知,蒙古族素有讲述故事与演唱史诗的文化传统,此中对于蒙古族英雄史诗的调查与研究,中外学术界历来关注较多,成果可谓丰赡厚重。相形之下,对于蒙古族民间故事的调查采录与研究,尤其对蒙古族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研究,囿于种种原因,长期处于清寂而薄弱的状态。对此,专注于蒙古族民间叙事研究的陈岗龙教授近来曾撰文就这一“失衡”现象进行了论及,这里不再赘述。基于上述原因,当我们重新翻阅并品味20多年前采录编辑的朝格日布与武德胜两位故事家的故事集时,难免会发自内心地慨叹:这两位身处蒙古族文化之“源”与“流”不同位点的故事家,已然以其各自的故事成就,成为蒙古族民间故事长河上耀眼的“双子”灯塔,其散发的璀璨光芒,至今仍辉映着现代社会与我们的身心世界。
今年是朝格日布老人诞辰100周年,武德胜老人诞辰94周年。在朝格日布老人的家乡——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党委和旗政府筹备“纪念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诞辰10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并以蒙汉两种文字公开出版《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故事集》之际,笔者拟就朝格日布与武德胜这两位蒙古族故事家的故事特征作以简略的分析与比较。

一、朝格日布与武德胜的基本信息概述
世人对朝格日布与武德胜这两位蒙古族故事家的了解与关注当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朝格日布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宝日和硕苏木海岱嘎查人,1912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牧民之家。他8岁当喇嘛,45岁还俗。朝格日布一生喜欢听故事和讲故事,他的故事主要是从喜欢讲故事的喇嘛师傅那里听来的,还有就是他多年来四处留心八方倾听各地流传的各类故事。朝格日布喜欢故事已近痴迷的程度,从小到大,他走一处,听一处,讲一处,年积月累,掌握的故事类型丰富多样,讲起来滔滔不绝,是当地蒙古族民众喜爱的故事家。除讲故事之外,朝格日布还擅长佛教查玛舞的表演,是其家乡附近几座寺庙最好的查玛分(跳神领舞)。1982年,朝格日布在内蒙鄂托克旗有关部门举办的讲故事比赛中获奖,随后,伊克昭盟文联民研会对朝格日布老人的故事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采录整理,出版了内部资料集《老故事家朝格日布讲述的故事》,收入老人讲述的各种长短篇民间故事54则。此后,朝格日布讲述的一些故事还被陆续收录进其他民间文学作品集中。据统计,朝格日布生前仅有59则故事公开出版,而他肚子里究竟有多少故事,至今已无人能说清。
武德胜是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哨乡十家子村人,1918年出生于一个农耕之家,1997年7月去世。武德胜生前不仅务农,还是个技术高超的瓦匠。他头脑聪明,多才多艺。能写善画,还会“抓像(泥塑佛像)”,精通蒙文,懂藏文,能读汉文,其故事都是用蒙语讲述。当然,他的最大天赋以及人生的乐趣还是在民间叙事的演唱方面。武德胜能讲述209则故事,演唱112首蒙古族民歌。他的曾祖父双喜、祖父札木苏、父亲宝音额木格其都是名闻遐迩的“好力宝”,歌手,都擅长讲故事。武德胜的故事主要是从祖父、父亲那里听来的,同时,他还向同村福寿寺内名为五斤的喇嘛学唱民歌和吹、打、弹、拉,又曾拜民间艺人特西日夫为师,大大提高了演唱民歌和讲故事的技巧。武德胜有一副高亢明亮而又婉转甜润的好嗓子,家有祖传的四胡,他常常自拉自唱,能连续唱一个通宵。有一次武德胜与一位民间歌手赛唱,两人从太阳落开始演唱,一直唱到第二天太阳出,那位歌手的歌已悉数唱尽,但武德胜的歌还滔滔不绝,此事在当地一时传为美谈。武德胜生前每到三伏挂锄或数九隆冬农闲季节都应邀到附近各艾力以至外乡去讲故事,唱好力宝,往往一冬天不着家,直到腊月过小年才赶回家去祭火。他在各地演唱好力宝,讲故事的同时,注意留心收集当地流传的故事,然后将这些故事融会贯通,精心打磨,使其更加完美完善。1987年,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印了《武德胜故事集》,收录他讲述的84篇故事,由朝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干部乌忠恕采录并翻译成汉文。
将两位故事家视为蒙古族民间故事长河的“双子”灯塔,主要基于他们的故事成就及其特殊的学术价值。朝格日布与武德胜都堪称蒙古族的优秀故事家,两人讲述的故事不仅数量众多,且质量皆在上乘,两人的故事活动影响皆辐射其家乡方圆百里,深得民众喜爱,广受赞誉,之于蒙古族民间叙事的传统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种水准的故事家在今天已属凤毛麟角。若就这一组个案的学术价值而言,在当下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视域,更是可遇而不可求。

二、朝格日布的故事与蒙古族文化之
“源头”景观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民间故事本是人们的行为和思维在其所直观感知的生活世界的一种构形,人的行为和所处的时空背景相互作用,相互阐释,从而才产生故事的意义。因此,故事文本中展演的一定区域内的民众生活图景便体现为一种文化的行为体系,故事空间也可以视为区域性“小传统”社会的缩影。
作为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几近同龄的两位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与武德胜故事的总体根系虽然具有一脉相承的蒙古族文化特点,但两人在具体故事的展开与处理呈现方面,却又分别体现出蒙古族文化“源”与“流”不同位点的特征,可谓“各美其美”,相映生辉。
朝格日布是土生土长的鄂尔多斯草原之子,是具有代表性的游牧蒙古族故事家。他的故事根基深扎于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古老土层,若依据故事的来源属性划分,可以说既有源于书面的故事,也有传统的口头故事;既有源自印、藏的民间故事和汉族民间故事,也有地道的蒙古族本土故事。此中后者蕴含有大量的蒙古族原生文化要素,凸显着蒙古族文化“源头”的特质。
朝格日布的故事大都取材于蒙古族传统的游牧生活,情节带有切近生活的特点,一些故事源头久远,蕴含着独特而深厚的蒙古族传统文化内涵,折射着草原游牧蒙古族对区域历史和自然生境的生态认知与生存体验,体现着蒙古族的一些古老的思维与哲学思想。
以《求子的老两口》为例,故事讲的是无子女的老两口在神通的喇嘛帮助下有了一个女儿,女儿成年时,父亲许诺谁能猜中女儿的名字,就把女儿嫁给他。恶魔蟒古思耍手段猜出了姑娘的名字,想娶姑娘为妻。姑娘听从家中骏马的话逃跑,女扮男装,却被识破性别,嫁给一位王子,后生下金胸银臀的儿子。然而蟒古思继续以偷换信件等手段对她进行加害,姑娘被迫携幼子出走沙漠。骏马死去,姑娘按照马的吩咐,割下马头埋葬,马头上神奇地长出一棵檀香树,母子俩爬到树上,追来的蟒古思砍树,狼和狐狸来骗蟒古思,最后喜鹊给姑娘的家里送信,从小陪伴姑娘长大的两条狗赶来,在危急时刻咬死了蟒古思,母子最终获救,过上了幸福生活。陈岗龙教授在《简论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讲述的故事类型》一文中对这篇故事的类型特点予以了分析,将其定位为复合型魔法故事。若以这篇故事的内容特征来看,可以说这是一篇带有鲜明蒙古族文化印记的故事,从中可以提取诸多反映蒙古族古老意识与文化观念的母题及关键词,诸如:未卜先知的喇嘛、恶魔蟒古思、猜少女名字、神奇宝马数次救主、父亲十八岁时用的磨刀石、母亲十八岁时用的梳子、成年少女的镜子、宝马施魔法建造蒙古包、女主人公生下金胸银臀的儿子、马头骨长出檀香树、动物与鸟类助人、爱犬为主人除害等等。而这些母题及关键词,在朝格日布讲述的《安岱莫日根和额日勒岱博格达》、《国师》、《尼姑敖敦巴拉的故事》、《宝如勒岱老人的儿子》、《每天早晨谈论昨天的梦的父子俩》、《得到三个宝物的故事》、《阿日吉·宝日吉汗》、《喜地呼尔》等魔法故事中都有大量表现,这类叙事情节的推演基本上都表现为借助某种“超人间”、超自然的神奇力量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情节也多是以变形、禁忌、魔术、感应、咒语、灵魂不死等古老观念为基础构建的,这正是蒙古族文化传统的突出表现。
众所周知,蒙古族民间故事受印、藏故事,特别是佛经故事的影响较深,这种影响主要源于佛教在蒙古高原长久而又深广的播布。借助于喇嘛僧侣们的讲经及注释佛经故事的多种编著文本,大量印、藏故事尤其是佛经故事在蒙古族民间广泛流传。朝格日布本人当过30多年喇嘛,他讲述的许多故事都可以追溯至佛经故事的古老源头。陈岗龙教授对朝格日布的故事进行研究发现,《尸语故事》、《三十二个木头人的故事》、《育民甘露注释如意宝饰》等文献是朝格日布讲述的印、藏民间故事的主要来源,在朝格日布生前出版的59则故事中,源自《育民甘露注释如意宝饰》的便有《被狐狸奚落的裸妇》、《麻雀的故事》、《冤枉的七只虱子》、《猫喇嘛念经》、《在青色油漆上打滚的狐狸》、《乌龟和猴子》等11篇故事,约占其出版故事总量的五分之一。朝格日布在讲述这些源自印、藏的故事和佛经故事时,注意将其本土化,结合蒙古族地区的生活特点和人们的欣赏趣味作了一定的世俗化处理,使这些外土的故事无论从人物形象塑造到生活环境的描绘,从情节的构成、表述的风格及至主题的呈现等方面,均带有比较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与蒙古族文化韵味。
美国人类学家沃德·古德纳夫指出:文化存在于文化持有者的头脑里,每个社会的成员头脑里都有一张“文化地图”,该成员只有熟知这张地图才能在所处的社会中自由往来。人类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张“文化地图”。朝格日布的故事向我们逼真地勾勒了草原蒙古族社会的生活镜像及“文化地图”。游牧族群的衣食之源都是向草原索取,草原上的动物及牧放的牲畜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和生活资料,因而,对动物形貌和习性的认知,是获取生存资料的必要条件。以游牧为生计的蒙古族民众,久已形成了对各类马匹的丰富认知,能够准确识别马的各种门类及毛色,谙熟马的各种习性,在蒙古族文化体系中,大量的文化符号也是以马作为“表现体”的。在朝格日布的故事中,动物故事占有相当的比重,尤其故事情节的演进与“马”的关联很多,对马的称谓繁复别致,饱含感情。诸如:水清草美中嬉戏的蜡白草黄宝马,四蹄生风的亮鬃草黄马,套沁花斑马,绿獠牙笼头金黄马,风轮雪里站枣骝马,金黄色毛的坐骑,二岁子铁青马……这种表述,在汉民族民间叙事中是难以想象和无从寻觅的,在长期的生存适应中,草原蒙古族民众已经建立起对生境中各种事物的认知系统和范式,草原生境中的多种物类各得其所,并逐渐衍化出各成系列的文化象征符号,此类表述在朝格日布的故事中可谓比比皆是。例如,游牧群体出于逐水草而居的生计需要,往往对居处地的方位有比较准确的把握,朝格日布的故事中常见这样的描述:“东南日出方向的宝日勒岱老头儿有个儿子叫宝日胡。西北方向的白噶日玛萨迪可汗有个女儿。跟她相比,我们连人家一根手指头都不如啊”;“日出东方察合台汗的独生女长的像阿米岱佛一样美丽,像满月一样生辉”;“与西北落日方向的白噶日玛萨迪可汗的女儿指腹为婚”;“去迎娶日出方向的娜仁仙女”;“黄昏十分,让儿媳骑一头黑驴,戴上一顶纸帽,绕着皇城反转三圈。最后,把她往不好的东北方向放逐……”再如,游牧群体对动物有着特殊的感情,许多动物不仅是牧人的衣食之源,也是其精神信仰中崇信的神偶与对象。朝格日布故事中的一些描述经常以马、牛、羊等动物作为表现体:描述时间过了很久——“只见拴在檀香树上的白马已经瘦得没法看了”;描述英雄的绝艺——“能把奔跑中的黄羊的舌头拔下来,卧着的兔子的睾丸摘下来,而且能做到让它们浑然不觉”;形容英雄的神功——“能追踪十天前走过的蜘蛛脚印,二十天前走过的蚂蚁足迹”;渲染英雄的武力——“额日勒代博格达抓住一头青牤牛的犄角,往两边一掰,抖搂清理它的内脏,在火上烤着吃……”还有一些故事借人格化的动物来表述蒙古族民众的是非善恶观念,情节鲜活而又生动有趣,极富讽喻意味。
不难看出,朝格日布讲述的故事带有浓郁的游牧蒙古族文化特色,他的故事中的画面几乎囊括了草原日常生活的全部场景。由于这些故事寄托着游牧蒙古族民众的精神期待,表达了他们理想的人生模式,涵盖了草原社会的意识形态特点,因而也构成了特定区域民众用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解释学体系。

三、武德胜的故事与蒙古族文化之
“流变”样态
与朝格日布相比较,武德胜是具有代表性的农耕蒙古族故事家。他与朝格日布集散故事的文化背景有着很大不同,而背景分析是理解人类行为的基础。
武德胜的祖上系蒙古族乌梁哈部落,该部落自1635年便从阿尔泰山迁移到东蒙地区,在辽西建立起喀喇沁左翼旗,迄今已370多年。东蒙区域的蒙古族族众由于长期与汉族农耕民杂居共处,早已顺应所处的区位生境,放弃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习汉民定居一处,主要从事农耕生计。武德胜是土生土长的东蒙族群后裔,其家族数代与汉民族杂居共处,文化彼此交融,其故事的根基既与蒙古族原生文化盘根错节,又吸收有汉民族与农耕文化的滋养,蒙、汉文化及游牧与农耕文化混合杂糅的影响十分突出,其故事凸显着蒙古族游牧文化的“流变”样态。
东蒙民间素有“讲故事解心闷,猜谜语显智慧”之说,当地民众酷爱听讲故事和好力宝。武德胜出生于演唱好力宝的世家,他秉承了蒙古族擅讲乐唱的民族天赋与传统,在讲故事方面尤其体现出较高的文学修养和艺术才华。作为蒙古族后代,武德胜的故事仍保留有较明显的游牧文化的叙事风格与韵味。以他讲述的《一个斑秃和七个亮秃》故事为例,这是一则地道的蒙古族传统故事,属于AT1535《富农民与穷农民》类型,与朝格日布讲述的《七个好吉格日和一个莫吉格日》是同一个类型的故事。会唱好力宝的武德胜讲起故事来这样开头:“在须弥山还是一个土丘的时候,在参天大树还是一棵小草的时候,在大海还是一个小洼的时候,敖包的东边住着一个斑秃,敖包的西边住着一个亮秃。他们都以打造勒勒车为生……”不难看出,武德胜的这种讲述风格,依然保有蒙古族演唱史诗的叙事古风。而此则故事中将从龙宫获取的宝物设置为马群,表述的仍是游牧民族的价值观。还有,故事中的勒勒车工匠、偷马贼等人物,以及马群、套马杆、皮口袋等器物,也系草原生活景观的写照。毋庸置疑,抱守和延续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古老传统,仍然是武德胜故事的特征之一。武德胜讲述的《太阳和月亮为啥是两口子》、《爱唱歌的牧日根》、《哈莫日玛额吉》、《铁木真和雪莲花》、《蒙古人为什么供关公》、《桑布和龙女》、《马蜂、老虎、猴子和塔日沁》等故事,都蕴含有蒙古族文化的某些原型与核心观念,彰显着人类文化原型的恒定性。
民间叙事的传播是以人为载体的,可以想象,武德胜的先人们当年负载至东蒙地区并传给后代的,应该是带有蒙古族游牧文化特征的民间叙事作品。同时,人类的文化心理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中产生并形成的,作为一种深层心理结构,也具有某种稳定性与承继性。在东蒙的土地上,由游牧生计转为农耕的蒙古族民众虽然面对的自然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在原有生境中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却很难改变,仍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着作用,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继续影响着族群的文化建构与走向。从宏观上看,武德胜与朝格日布的故事在主题与文化观念方面仍然暗脉相通。草原游牧文化的恒久影响,使得两人的故事主题都较多地缠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性善恶的冲突方面,重教化,尊传统是两位故事家大部分故事的叙事宗旨。
然而,蒙古族乌梁哈部迁移东蒙之后,毕竟远离了逐水草而居,守草原行猎的生存条件,东蒙区域的地理条件与资源结构,使其只能以耕读世其家。在与汉民族长期的杂居共处中,汉族文化与农耕文化的长期浸润,使东蒙地区蒙古族民众的文化心理自然融入了汉族农耕文化的观念与意识。与此同时,在历史长河的淘洗颠簸中,一些曾孕生于蒙古族游牧文化“营养基”的古老神话、传说与故事,由于在东蒙的农耕生计中失去了附着物而渐渐湮没;某些在蒙古高原上曾风云一时的历史人物,在东蒙地区,也由于文化土层瘠薄鲜为人知而渐渐失传。没有湮没和失传的,是那些蕴含着蒙古族文化古老观念的传统故事。这些故事至今仍流淌在东蒙的蒙古族民众口耳之中,其生生不息的传承动力,即在于这些故事隐括了蒙古族民众最基本的情感模式。
将两位故事家的故事稍作比较,便可看出,武德胜讲述的许多故事已同草原游牧蒙古族的文化拉开了某些距离,呈现出“流变”的样态。例如,武德胜的家乡是印、藏佛教信仰的辐射地带,武德胜与朝格日布的人生经历不同,他没有当过喇嘛,在他的故事中,我们虽然依旧可以捕捉到弥漫于蒙古族社会的佛教信仰传统及其精神制约,但同时也能领略到东蒙的蒙古族民众在这些信仰和制约面前表现出的或庄严、或轻慢、或敬畏、或戏噱的复杂心态。尤其一些故事还借助叙事题材,表露出迁移东蒙的蒙古族民众对“本土”蒙古族的某些带有世俗性的复杂看法。以《二喇嘛驱鬼》为例,故事开头这样说道:
喀喇沁有个不学无术的酒肉喇嘛,在本地吃不开想到坝后去糊弄老蒙古(东蒙地方性话语,对游牧蒙古人的称呼,笔者注)。正走着,碰上一个土默特的喇嘛,原因和他一样,也想到坝后去骗钱。因为他听说坝后老蒙古心实,好糊弄。两人商量好互相配合,一个冒充葛根活佛,一个冒充徒弟。两个喇嘛招摇撞骗,来到坝后……
再以武德胜讲述的《额尔敦扎布和神蛙》为例,这则故事讲述的是敖木伦河里的神蛙保佑着两岸风调雨顺,民众生活美满。外国的鬼头企图盗走敖木伦河里的神蛙,神蛙在善良的蒙古人额尔敦扎布的帮助下,最终除掉了外国鬼头,额尔敦扎布也因此得到了神蛙的酬报。从这则故事的内容与形式来看,应该说还保有蒙古族故事传统的叙事套路与叙事风格。但在故事的深层结构,即故事隐含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方面,却已悄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故事的结尾,武德胜这样描述神蛙对主人公的酬报:
“额尔敦扎布家里很穷,别说猪,家里的耗子都饿跑啦。他哼哈地答应下来,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夜里,突然一阵猪叫声把他吵醒了。他急忙到院子里一看,嗬,满院子都是挤挤喳喳的肥猪,少说也有二百口哇!额尔敦扎布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啦!他连忙杀了一口肥猪,请了一桌客,找到河滩主人,写了文书买了地,他把其余的肥猪卖掉,换回来米面布匹。转眼日子就富裕起来。这年夏天,敖木伦河发了场大水,在河滩上淤了一尺多厚的黑泥。上千亩的沙滩一下子变成了肥沃的良田。嘿!那土头儿才壮呢!攥一把嘀嗒油。额尔敦扎布全种上了荞麦、黍子。他牢记白胡子老头儿的话,勤勤恳恳干活,莳弄庄稼,偏赶上这一年风调雨顺,到了秋天,千亩河滩获得了大丰收。他一下子打了千石粮食,盖了一片瓦窖似的房子,拴了四套骡子车,小日子过得扑腾扑腾的。”
显然,故事的落点张扬的已是宗法制小农社会的人生理想,与游牧文化传统的个体价值、人生理想、财富追求全然没有了干系。
武德胜的故事讲述风格和朝格日布相似,两人在讲故事时皆重绘声绘色地语气渲染,都属于那种能从容地利用故事结构来牵制听众,以情节取胜,颇具风度的大故事家。武德胜讲起故事来可谓字字珠玑,谚语、俗语、名言、俚语随口而出,俯拾即是。如形容官吏之坏,他随口说:“诺谚信不得,湿柴烧不得”;讲到交通行走,他说:“与其骑劣马,不如拄拐棍儿”;在他的故事中,更有大量脍炙人口、具有蒙古族文化特色的哲人睿语,格言蒙谚,诸如:“驴见了灰堆总想打滚儿”;“狼咋饿也不吃白菜”;“狐狸找不到肉便说自己修好封斋”;“让你胖起来的是羊肉,让你穷起来的是白音”;“白音谈姑娘,穷人谈饥荒”;“跟野狗打架保不住袍子,跟王爷打架保不住脑袋”;“只要你老老实实,坐牛车也能撵上兔子”;“吃掉的青草能长出来,吃草的牙齿却迟早脱落”;“人只要活着就能使金碗喝水”……
这些美不胜言的带有民族语言风格的表述,使武德胜讲的故事格外具有艺术感染力。
同为蒙古族民间故事的传人,朝格日布与武德胜分别为我们提供了文化的固守与移动对文化主体及其发展有何影响的两种鲜活形态。解释人类学的代表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因而,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故事家由于彼此生存环境、经历、信仰、价值取向不同,性别、年龄、文化、个人资质各异,在故事活动中,无一例外地体现出各自的风格与特点。从这一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每一位故事家所展示的“文化之网”都是独特的,因此,我们在对故事家进行研究时,不仅要对其进行现象的、客观的、直观的意义的研究,即研究他们故事的文本、类型、数量以及故事风格、传承线路、听众反映等方面的特点;同时,还应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转向对非直观的、对故事家的传承活动具有深层的制约与影响作用的某些相关因素的探讨。诸如:故事家的知识构架对故事文本具有怎样的作用与影响?故事家是依据怎样的文化原则对文本进行重构的?故事情境对文本有着怎样的作用与影响?作为区域性民间文化的代表人物,故事家所展示的文本世界折射着该地域民众怎样的一些文化观念及文化心理等等。若循此思路追问与探究,对朝格日布与武德胜这两位蒙古族故事家的审视、比较与研究还可以在更多的维度展开。对这两例个案的解析,可以为学术界提供一种超越地域与民族的局限而具有普适性价值的研究范例。但限于篇幅,本文在此只能作一孔之窥。
文章原标题:蒙古族民间故事长河的“双子”灯塔——朝格日布与武德胜的故事特征比较
(详细注释请参照原文)
文章来源:《故事家朝格日布讲述的故事》
白音其木格、策·哈斯毕力格图 搜集整理
乌云格日勒 译
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 上一篇: 回忆蒙古骑兵赵那斯图革命经历
- 下一篇: 内蒙古发现国家一级文物 《蒙古农民》创刊号(蒙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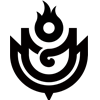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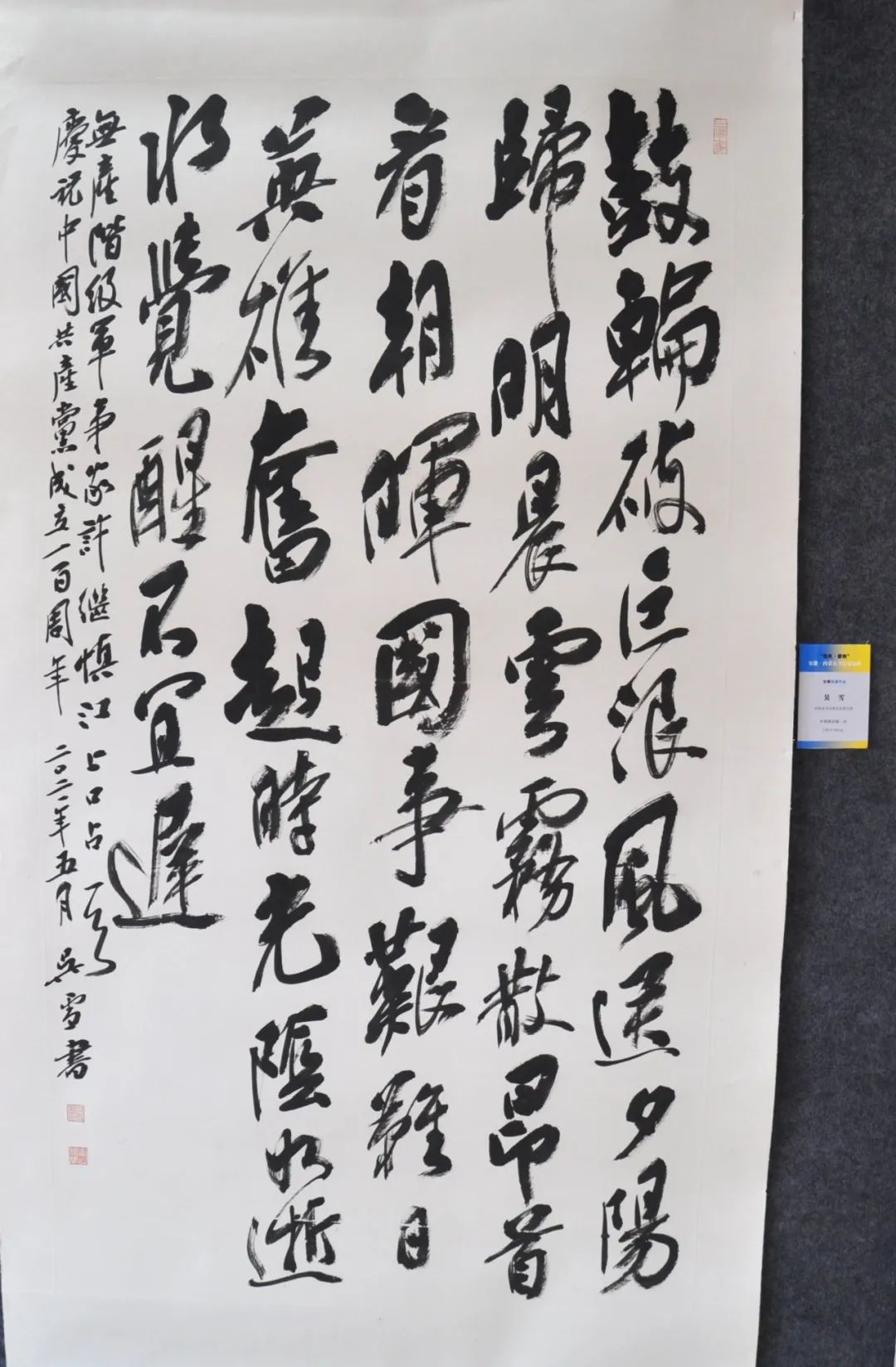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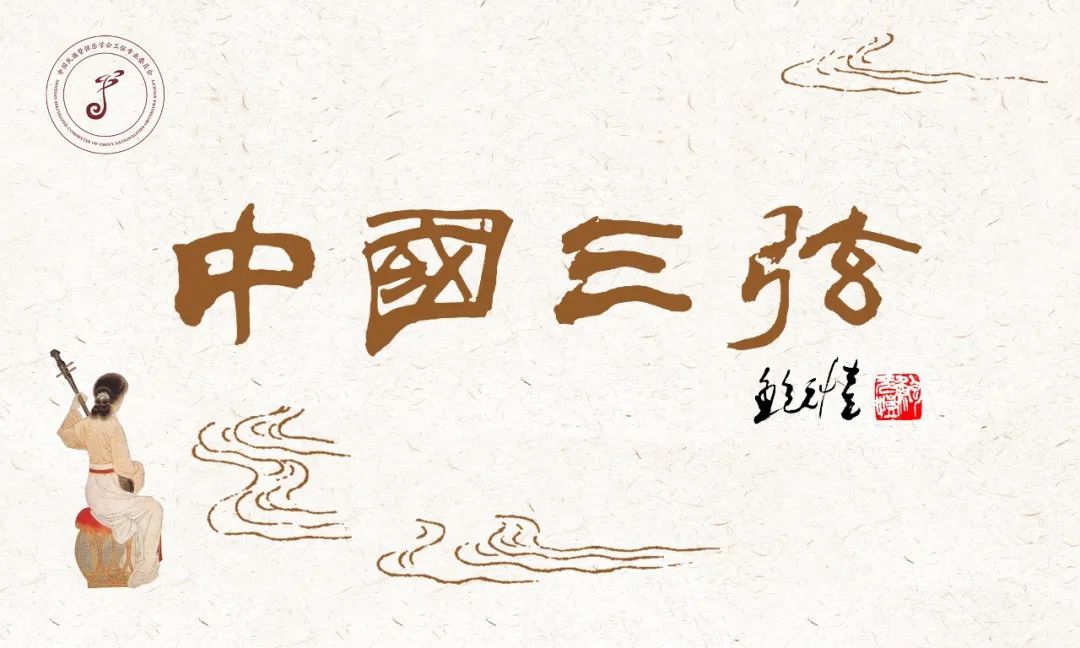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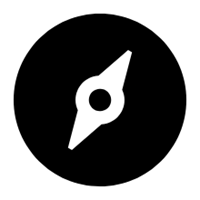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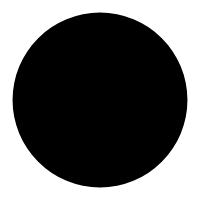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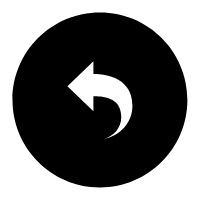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