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当低音四胡伴着胡尔齐那沧桑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我全身的血液就会往上涌,喉咙里总有什么东西堵住似的,因为在那乌力格尔里,在那低沉的乐声里,在那浑厚的男中低音里,有我的童年时光和少年情怀……
第一次听乌力格尔
我八九岁时,在冬天里的一天,村里来了一位胡尔齐(蒙古说书艺人),晚上在大队的五间筒子房里演出。平时在大队那筒子房的长长的炕上,只有看大队的光棍老爷爷一个人住在炕头,我们小伙伴们一见到老爷爷,大老远就喊爷爷,爷爷看我们一眼,也不答话。晚上早早吃完饭,跟着哥哥去听乌力格尔,这可是我第一次听乌力格尔。
一进大队屋里,灯火通明,屋里挂了四盏保险灯,在没有电灯的时代,这是我见到的最亮的晚上。全村老小挤满了五间大屋,有坐炕上,有坐凳子上的,也有直接坐在地上的,屋里充满了烟丝味、汗臭味。人们一边磕着毛壳,一边又嘻嘻哈哈的说笑,女人们用头巾裹着脸,探出两只眼睛,对男人们的荤嗑假装没听见。这时胡尔齐还没有登场,一定是在村书记家吃饭呢。过了好长时间,人们开始骚动起来的时候,胡尔齐在书记的引领下走进来。
胡尔齐着一身蓝色蒙古袍,戴一副墨镜。平时我们见不到谁穿蒙古袍,只有乌兰牧骑演出的时候能看到舞台上穿的蒙古袍,所以有人穿着蒙古袍,着实新鲜抢眼。胡尔齐被书记牵着手走上炕中央,坐在早已准备好的椅子上,这时我才发现他是个瞎子,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头,有点清瘦,头发有些乱。书记介绍说胡尔齐的名字叫天仓,住的村庄离我们村不远,但现在已经记不起来是哪个村庄了。天仓小时因得眼疾而致盲,因此学四胡说书,当了胡尔齐算是有了一技之长,日后可说唱乌力格尔来养家糊口。
田仓胡尔齐的四胡音色最洪亮,是我至今听到的四胡中最洪亮的。四胡的颈上挂着四个颜色的飘带,随着四胡的摆动摇曳着,就像蒙古摔跤手项上带的精嘎一般。他说书的声音也像他的四胡的声音一样洪亮,稍稍带点沙哑,但吐字很清楚。他讲的乌力格尔好像是《杨门女将》,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他演唱的将军着装披甲的段子最为精彩,引人入胜。可是不知为什么,田仓胡尔齐只讲了两天便走了,后来听说他讲得乌力格尔有点乱,大人们听不下去了,而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只是看热闹而已。
田仓胡尔齐也许最终没能成名,因为后来再没听到他的行踪他的乌力格尔。但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胡仁乌力格尔,所以对田仓胡尔齐印象极深,至今都能记起他说书时的一颦一笑,还有那浑厚透亮的四胡声。
讲哲学的胡尔齐
自从田仓胡尔齐来过村里以后,村里开始经常有胡尔齐来讲乌力格尔,但是说唱地点要是在个人家的时候,父母一般不让我们兄弟去,尤其是我岁数小,哪儿都不让去,怕我们又惹出什么事端来。
一天村里又来了一名胡尔齐,名字叫巴特尔朝克图,此人是父亲的好友即内蒙古著名表演艺术家包树海的朋友,包树海常向父亲提起巴特尔朝克图,说他德艺双馨,才华横溢。当父母听说是他来村里说唱乌力格尔,决定让三哥领着我去听。乌力格尔说唱地点设在我们村西头新盖完四间大筒子房的老赵家,我跟着三哥去老赵家,看见满屋子全是人,闹轰轰的。我看胡尔齐是位瘦瘦的干巴老头,穿戴很朴实,但两眼深邃有神,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带有一股子学者的风度和气质。胡尔齐说的是《狸猫换太子》,大概说了十多天。一天,吃完饭我早早来到老赵家,坐在胡尔齐不远的地方。村上一位长者叫温塔热的,陪着胡尔齐唠嗑,胡尔齐一边呷着茶,一边和温塔热老人唠嗑,我看见他拿起茶杯说,这个茶杯即使碎了,但它还会以其他的形式存在,世界上的物质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只是茶杯的形态变了而已。后来长大读书后想起这段情节,原来胡尔齐给温塔热讲的是物质不灭定律(质量守恒定律)。我当时觉得他讲的东西很神奇,和父亲经常给我们讲的道理差不多,所以在旁边一直听得入神。胡尔齐讲了好长时间,忽然抬手指着旁边的我问温塔热老人:“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个孩子以后一定不一般,将来一定会有出息!”或许胡尔齐想奖赏一下他的忠实听众吧,说了这么一句话,却让我一直记到现在。
许多年之后,我才有机会更深的了解巴特尔朝克图胡尔齐。他年青的时候在通辽念过伪满的高小,有较深的文化底蕴,在科左中旗有着很好的口碑,民间赞誉之词颇多。当初他家庭条件不好,可是牧主的姑娘看上了他,便不顾一切,与家庭断绝关系跟了他这个贫穷的小伙子,“文革”中又因他在伪满政府中任过职,因而又跟着吃尽了苦头。然而他们的爱情故事却成为一段佳话,令人们赞叹不已。由于巴特尔朝克图孩子多,想在农闲时间里打打工,挣些外快来补贴生活,可是那个年代哪有那么多的零活可干呀,便把年青时学的四胡拿出来,开始学说唱乌力格尔,以此换些粮食来解决全家的温饱。
可能是因为夸过我一句的缘故吧,我对巴特尔朝克图胡尔齐念念不忘,后来在收音机里再一次听完了他说唱的《狸猫换太子》,至今难忘。
收音机与乌力格尔
收音机在那个年代是“四大件”之一,只有娶媳妇的家,或是经济条件好的家才能找关系买上一台。村里开始有了收音机之后,人们都聚在有收音机的家,听广播电台里的胡仁乌力格尔。我经常跟着三哥去我姨家听收音机里的乌力格尔,每晚都要去。有一次在听乌力格尔的时候,外面下起了雨,回家的时候鞋子里灌满了泥浆,母亲便决定要买一台收音机。之后我们家每天卖一点牛奶,积攒到了28元钱,买了一台羚羊牌收音机,从此我们在家里听收音机听乌力格尔了。
每天下课之后,同学们四散跑回家,怕误了乌力格尔的时间,那时乌力格尔是我们生活的全部,要是落下哪怕是一分钟的段儿没听到,都会觉得遗憾终生。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有百锁胡尔齐说唱的《十五贯》,有布仁巴雅尔胡尔齐的《隋唐演义》、《龙虎头》、《刘秀传》,有海宝胡尔齐的《烈火金刚》、《呼延灼》、《平原枪声》,有希日布胡尔齐的《封神演义》等诸多乌力格尔。那时班里有个同学叫邦柱,最能模仿胡尔齐学唱乌力格尔,下课之后全班同学都围上他,央求他给大家讲一段。他就会盘腿坐在拼起来的板凳上,操起班级扫地用的笤帚当四胡,不知哪个同学这时早早给他找来一根树枝当四胡的弓子,他就开始摇头晃脑的说起乌力格尔来。这时全班马上会静下来,我们会随着他的演唱开始穿越时空,横刀立马,驰骋疆场,攻城掠地,刹那间血光四溅,人头落地。虽然邦柱学习成绩一般,又不能打架,但在班里地位较高,是因为他有演说乌力格尔的本领,因而倍受大家的尊重。后来邦柱因传染上狂犬病而殁,否则也许会真的成为一代胡尔齐大师吧。
收音机里听到的乌力格尔不仅说唱艺术精湛,而且故事演说严谨。在收音机里我们听到了正宗蒙语乌力格尔版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演义》、《隋唐演义》、《三侠五义》等中国名著和著名评书演义。乌力格尔的翻译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在不改变原著的基础上,如何做到作品的本土化、民族化,让听众接受,绝非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能做得来的。蒙古说书艺人将汉语评书改编过来演说的时候,会结合蒙古民族的文化和伦理,有所增减,使故事本土化、民族化,使汉语语境下的故事演变成蒙语语境下的乌力格尔,听起来入情入理,听众更容易接受。据说有一位胡尔齐因为要准备说唱《三国演义》累得便血,听到这样的故事,总是令我对这些蒙古族的乌力格尔大师肃然起敬,是他们的无私付出,才有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胡仁乌力格尔。
如今,大师们一个接一个的去了天国,有时在广播里仍然听到他们早已录制的乌力格尔,眼睛会不由得湿润起来。我想在那个世界里一定会有乌力格尔的,不然怎么叫做天堂呢!
牙步根乌力格尔
牙步根乌力格尔是蒙古评书。多少年来,蒙古说书艺人都是拉着低音四胡,或是朝尔、马头琴说唱乌力格尔的,离开了乐器伴奏的乌力格尔一直以来让人难以想象。据说有一次,海宝胡尔齐录制乌力格尔的时候,有位汉语评书艺人跟他开玩笑说:“你们蒙古族胡尔齐离开四胡就说不了乌力格尔了”。海宝胡尔齐一时语塞,无言以答,因为现实中确实如此,蒙古族没有评书,也就是没有无伴奏的说唱。海宝胡尔齐自此开始琢磨,决心要演说没有四胡的乌力格尔,为蒙古乌力格尔探索出一条新路,丰富民族的乌力格尔文化。于是他将准备录制的胡仁乌力格尔《平原枪声》,改编成蒙古评书即牙步根乌力格尔,蒙古族的牙步根乌力格尔从此诞生了。
海宝胡尔齐不仅开创了蒙古评书先例,而且评书《平原枪声》一炮打响。小说《平原枪声》里的众多人物形象,被海宝胡尔齐演说得栩栩如生,如马英、王二虎等人的形象,描绘得个性鲜明,令人无限回味;故事情节讲得又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让人听完一节又盼着下一节。在众多听众心里,海宝胡尔齐的牙步根乌力格尔超越了他的胡仁乌力格尔,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海宝胡尔齐的牙步根乌力格尔填补了蒙古说书史上的空白,是蒙古族乌力格尔历史上的一个熠熠生辉的里程碑。
自海宝胡尔齐的牙步根乌力格尔之后,后继者较少,这是我的恐慌,也是众多乌力格尔爱好者的恐慌,我真诚期盼着有关部门能够重视和扶持牙步根乌力格尔,培养新一代牙步根乌力格尔的胡尔齐,让牙步根乌力格尔这朵奇葩在草原上常开不败。
在乌力格尔里,我找到了蒙古人固有的英雄崇拜精神,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中的仁义忠孝道德伦理,学会了打抱不平行天下公义之举……乌力格尔给了我童年的精神享受,也给了我无限想象的空间,同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忠诚、正义、善良和勇敢的种子。如今,每当我开着车行走在路上,就会打开车上的音响,放上一段乌力格尔说唱,我就会找到心灵的归宿。有时穿行在喧嚣的城市中,我会打开车窗,让世人也来听听这渐行渐远的乌力格尔,向世人证明在这电视电脑的独霸时代,还有人依然喜欢听乌力格尔!
乌力格尔,是我的心痛,是我永远的爱!(作者:包树海2012.10.6)
- 上一篇: 胡尔奇-小布仁巴雅尔简介
- 下一篇: 胡尔奇布仁巴雅尔对口头艺术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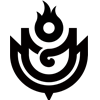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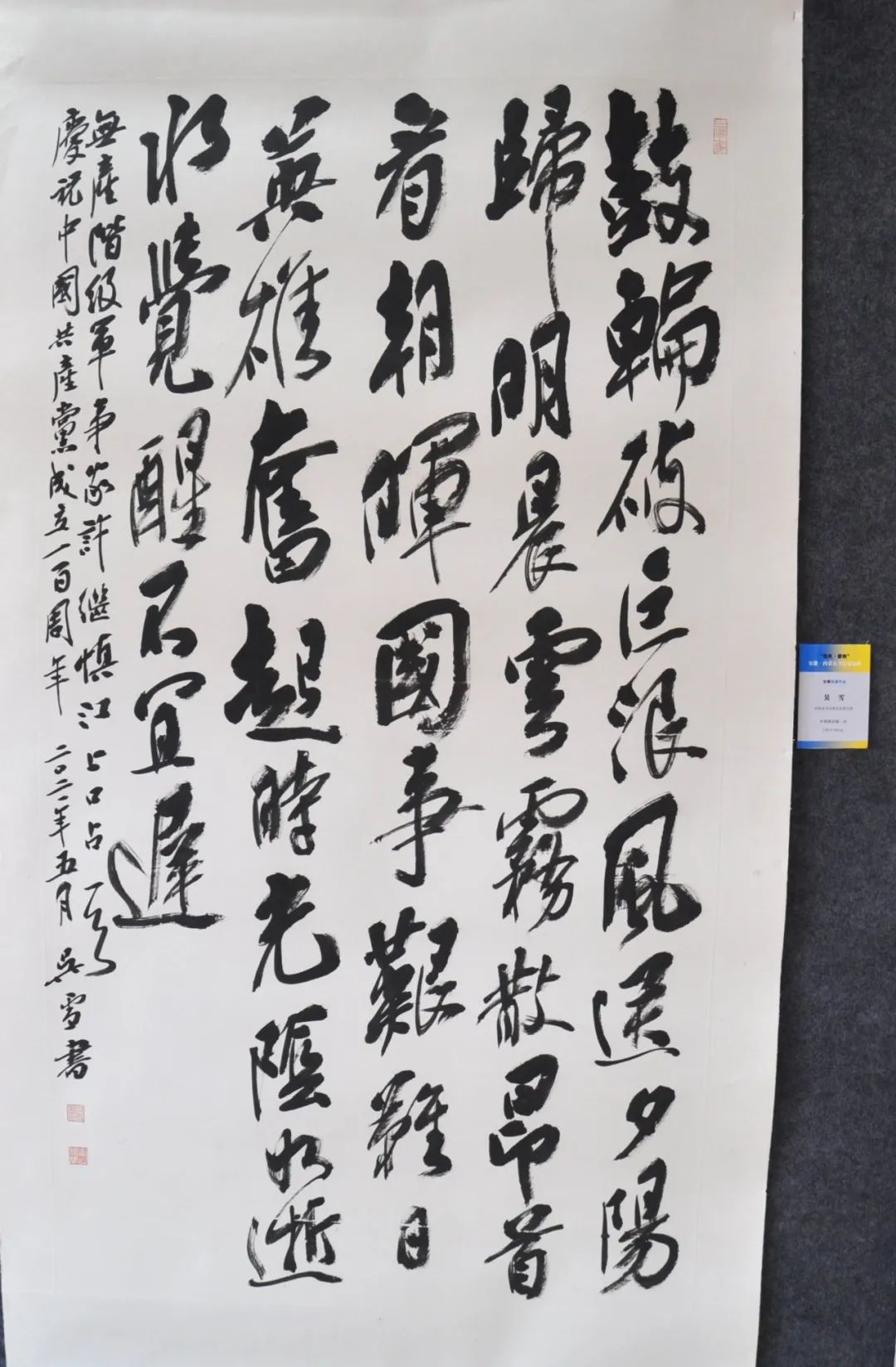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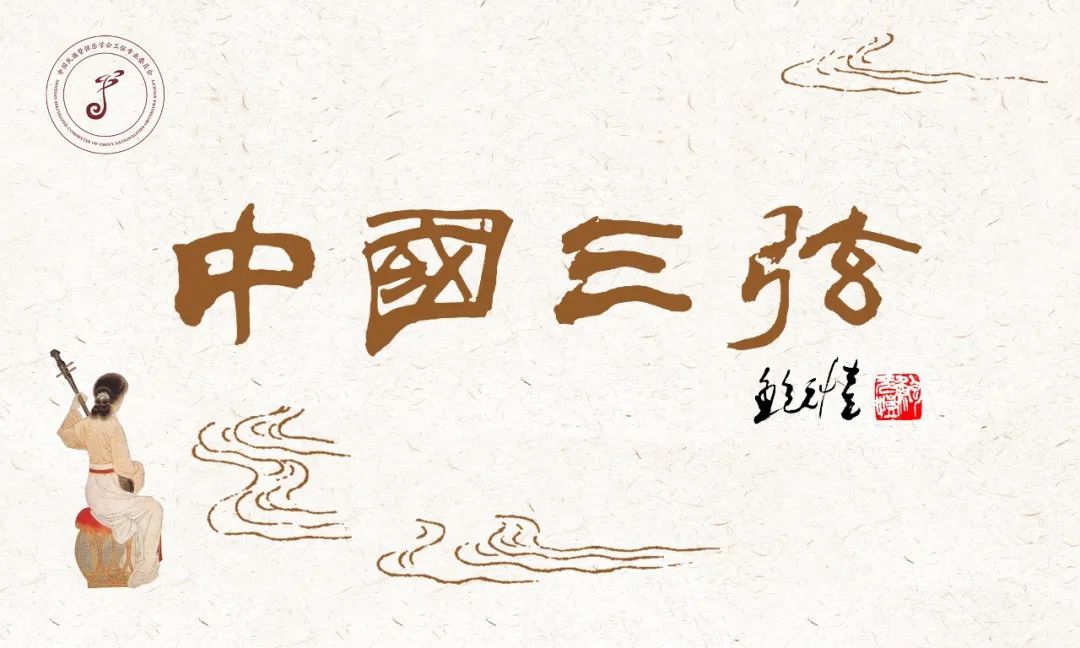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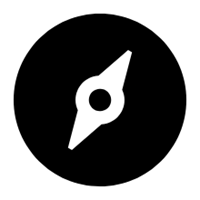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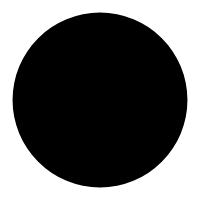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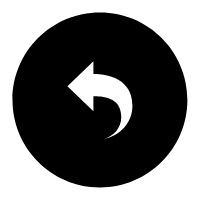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