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剌阿塔思”考释
宫海峰
摘 要:元代文献中出现的术剌阿塔思是一种特殊的马。术剌又译住剌、着力牙等,是蒙古语ǰoriya﹥ǰorā(ǰurā)的音译,突厥语作yorga。此种马匹要经过专人特殊训练,行走方式特殊,又称为“对侧步马” “蹿行马”,是不可多得的良马,故比普通马要昂贵很多。训练这种马匹的人称为拙里牙赤(ǰoriyači)。元廷在各地驿站中配备这种马匹提供给重要使臣使用,但是诸王等人的使臣、番僧等人却倚仗权势越级挑选和滥用蹿行马,甚至殴打站户,严重影响了驿站秩序。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元廷无奈下令驿站不得蓄养蹿行马。这也折射出元廷对诸投下管理乏术的一个社会问题。
关键词:主剌阿塔思 蹿行马 拙里牙赤 驿站
一、引言
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马是极为重要的。特别在古代,马匹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日常生活中,游牧民更离不开马匹,马对他们来说即是生产工具,又是生活的手段。在蒙古族中以马、牛、骆驼、绵羊、山羊为代表性的家畜。它们在《元朝秘史》中均已出现,如:秣驎(morin),旁译“马”(31节);忽客儿(hüker),旁译“牛”(100节);帖篾延(teme'en),旁译“骆驼”(244节);豁纫(qonin),旁译“羊”(19节);亦马阿惕(ima'at),旁译为“羖歴每”,即山羊的复数形式(151节)。蒙古人将这五种家畜又合称为tabun qošiɤu mal,意为“五口之畜”。在五畜之中,马居首位。
由于马匹与牧民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存关系都非常密切,所以牧民对马的观察也极为细腻。他们以马的齿岁、性别、毛色、个性特点、用途等不同角度分别给予不同的命名,相当繁杂。蒙元帝国统治的十三至十四世纪时期文献中也留下了不少有关马的不同称谓。如《大元马政记》中就记载了多个根据毛色称呼的名称:黑玉面马、五明马、桃花马、黑花、赤花、赤玉面、栗色玉面马等等。学界认为写成于元代的古本《老乞大》在描述一段马匹交易的对话中,记载了近三十种关于马的不同称呼,已有学者对此做过精密的考释。此外,在元末和明代编撰的各种译语中也记载了许多种马的名称,如《至元译语》的“鞍马门”,《华夷译语》的“鸟兽门”等等。可见在元代,普通的平民对马匹的各种称呼也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由此不难想象,作为元朝统治阶层的游牧贵族来说,对马匹会更加熟悉。前文提到的morin在蒙古语中是马的通称,可以指各种马。《秘史》中用蒙古语还记载了许多不同马的叫法,如阿黑塔(aqta),旁译“骟马”(123节,祥见后文);“可团勒(kötöl)”,旁译“从马”(99节);阿都兀(adu'u),旁译“马群”(124节);兀剌(ula'a)旁译“马匹”(199节),阿只儿合(aǰirqa),旁译“儿马”(指未阉割的公马,141节)。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在元代对马的称呼已相当复杂。其实不只这些,对于骑乘马匹的人来说,更为关心的是马的走法。具体的说,如骑在马背上是否舒适,马的耐力是否持久,马的行走或奔跑时速度快慢,马的性情是否温顺等等。仅就马的各种走法,在现代蒙古语中也有非常复杂的名称。其实早在《秘史》中已经记载了一些有关马匹的不同走法,如“朶卜秃勒周(dobtul-ǰu)”,旁译“走马着”(90节,56页),指快速奔跑;“合塔剌周(qatara- ǰu)”,旁译“点着”(32节),为小跑之意。骑乘马匹的人自然会喜欢选优良的马匹。如果驿站中的马匹存在优劣之别,乘驿的使臣势必会挑选良马,甚至会给驿站的管理带来影响。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元代一种有特殊走法的马匹,文献中称为“朮剌阿塔思”。首先对该译词进行还原和语音构拟,再考察该马匹的特点及在元代使用的相关情况。
二、前人研究情况
《至正条格》“条格”第41条中出现“朮剌阿塔思”一语。
马驼草料
至元四年四月,户部议得:“度支监关:‘柳林飞放马驼,除御位下,并各位下官头
口、朮剌阿塔思飞放合用马疋外,其余大象、打驼、驼骡、空闲马疋,拟合发回大都,
存留草料内喂养,听候回还,趁赶至彼,以备用度,不致重支草料,亦免科敛百姓之扰。’
合准所拟,为例遵守。” 都省准拟。
这里的至元应为元顺帝时期的后至元年号,即1338年。引文中出现的“朮剌阿塔思”一语,其中“阿塔思”较为清楚,其来源为突厥、蒙古语的aqta,意为“骟马”(即去势后的公马),阿塔思(aqtas)为其复数形式。元代文献中常见的“阿塔赤(aqtači)”为一专名,是在aqta-后接构成从事某一职务人含义的后缀-či构成,阿塔赤(aqtači)为专门管理骟马的人员。蒙古语中还有一个后缀-čin,用法与功能与-či很相近。这两个后缀除蒙古语族语言以外,在突厥语族及满通古斯语族的各种语言中从古至今都很活跃。元代蒙古语中的额勒赤(elči)为使者、使臣之意,它与《元史》中出现的突厥语人名牙老瓦赤(yalavači)同义。与早期蒙古人-室韦人具有共同族源的鲜卑人语言中也能见到这些用法,《南齐书·魏虏传》中记载:“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带杖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其中的鲜卑语词汇“比德真”、“胡洛真”、“乞万真”分别与元代蒙古语的音译词“必阇赤”、“忽儿赤”、“怯里马赤”对应,这些词语的后缀均为-čin。-či和-čin在古蒙古语中有时分别以表示单、复数的形式出现,如:“阿都兀赤 亦讷 巴歹(adu'uči in-u badAi)”(…的阿都赤巴歹,见169节),“巴歹 乞失里黑 豁牙儿 客额额速 扯列讷 阿都兀臣 阿主为 者(badai kišiliq ke'esü čeren-ü adu'učin aǰu'ui ǰe)”(巴歹、乞失里黑二人为扯连的阿都赤,见219节)。笔者认为-čin还应有表示范畴概念的含义,如“探马臣(tammačin)”,旁译为“官名”(273节)、“答鲁合臣(daruqačin)”,旁译为“镇守官名”(263节)。
关于“朮剌”,《校注本》指出,该词为蒙古语jura的音译,即《至元译语》中的“住剌(蹿行),并比对为《老乞大》中出现的“窜行马”。《校注本》还解释“蹿行”为“迅速奔跑之意”。在此之前,上引金文京教授等译注的《老乞大》中给“窜行马”注释为:“快速奔跑的马,《至元译语·鞍马门》中有‘蹿行,住剌’一词。‘住剌’为蒙古语ǰurā的音译,指轻快奔跑的马。”党宝海在《蒙元驿站交通研究》中认为:《元典章·兵部》“休拣窜行马例”中出现的“窜行马”当指能够快速奔跑的好马。还指出,该词即元刊《事林广记》“至元译语”中所收录,与汉语“蹿行”相对应的蒙古语词“住剌”,这个词就是蒙古语дулаа,有“疾跑”之意。
以上学者研究的观点,似乎可以这样看:1.几位学者均认为,《老乞大》及《元典章·兵部》中的“窜行马”即《至正条格》中的“朮剌阿塔思”,朮剌与《至元译语》中的蒙古语“住剌”为同词;2.认为“住剌”(即蹿行、窜行)为“疾跑”或“快速奔跑”之意;3.他们对“住剌”一词拟定的原词不同,有的还原为ǰura或ǰurā,有的为дулаа(dulā)。对于第1点笔者完全赞同,对于第2点笔者想做一些补充,第3点因为上述学者的观点不同,也想略抒浅见。
三、对“朮剌”一词的考释
根据前人研究已经知道“住剌”即“朮剌”,它们是某一个蒙古语词的同名异译。住和朮字在《蒙古字韵》中为床母和澄母,鱼韵,在《中原音韵》中均字为鱼模韵。可以构拟其读音为*ǰu。剌字在《蒙古字韵》中为来母,麻韵(未见《中原音韵》中收录该字),可以构拟读音为*la。在元代音译蒙古语的惯例中,剌字不仅可以译写la音,还可译写ra音,所以“朮剌”或“住剌”所标记的读音可构拟为*ǰura或者*ǰula。Дулаа(书面语形式为dulaɤ-a)的起首音d属于舌尖塞音,舌尖塞音d、t在蒙元时期一般用端母或透母字译写,如最常见的daruɤači译写为“达鲁花赤”,aldangqi译写为“按答奚”。《元史》中出现的地名“答兰版朱思”之野,实际上音译的是蒙古语dalanbalǰus,dalan为“七十”,balǰus为“多个沼泽”,该词在《秘史》中译写为“答兰巴勒主惕”、“答兰巴勒渚惕”(见129、201节)。再如,tammači与“探马赤”对应;tatar译写为“塔塔儿”等等。端母与透母字有交替使用的现象,这和蒙古语本身的情况也有关系。如“阔端赤”译写kötölči。似乎未见蒙元时期用床母及澄母字译写蒙古语d音的痕迹。如前所述,元时期的床母、澄母字一般对译蒙古语的ǰ音,如:ǰam/站、ǰemis/者迷失(果)、jiqasun/只合孙(鱼)、ǰoriq/勺里黑(意志),以上见《华夷译语》。ǰusaǰu/主撒周(住夏着);ǰügeli/主格黎(以竿悬肉祭天)。以上见《元朝秘史》。在蒙古语的第一个音节交替规则中,也几乎不见有舌尖辅音d与舌面前辅音ǰ交替的现象,较多见的有两个唇音“m”与“b”的交替。经学者研究,在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言中d、t音位在前高元音i的影响下有音变为ǰ、č的现象,如《女真译语》中的替和*tiho(鸡),和后来的满洲语čoko。 在古代蒙古语中有许多借自突厥语的词,凡突厥语中含有辅音-d的,在蒙古语中往往变为-ǰ。但在蒙古语内部辅音-d与-ǰ的交替现象似不多见。所以笔者认为,对朮剌读音的构拟,ǰura更接近真实。
那么“朮剌”、“住剌”对译的是哪一个蒙古语词呢?笔者认为该词就是现代蒙古语ǰiruɤ-a(口语形式为ǰoroo,西里尔文书写形式为жoрoo)的古音。关于ǰiruɤ-a,词典中的解释为:1、马在行进时一步举右侧双腿,下一步举左侧双腿,如此小跑前行。2、专指具有这种特殊走法的马匹。现在对这种马一般俗称“走马”,民间对行走技术良好的马称“有走儿”。德国学者多费尔(Doerfer)对突厥语yorga作过研究,解释为“快跑的对侧步马”,并指出在蒙古语中称为ǰiruɤ-a。他所说的是ǰiruɤ-a是指现代蒙古语。ǰiruɤ-a﹥ǰorō。
在《登坛必究》卷二十二所载《译语》的“声色门”中,笔者注意到列有一词“撺”,其相对应的蒙古语为“着力牙”。《卢龙塞略》“兽畜类”中还收录一词“窜,著力牙”。“着力牙”、“著力牙”(ǰoriya )与“朮剌”也是同一个词。ǰoriya﹥ǰorā﹥ǰurā。
除了以上所列在我国编撰的双语词典外,古代西方人编撰的词典中也有收录。14世纪后半叶,也即元末,在阿拉伯半岛西南端也门的拉苏勒王朝(Rasulid)编写一部《国王字典》(Hexaglot)。该字典包含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蒙古语等六种语言,用阿拉伯文字拼写。在该词典的蒙古语部分中收录了一词جوریا(ǰoriya),对应的突厥语为یریقا(yoriġa)。注释者解释为Ambler(horse),即“对侧步马”。笔者认为,جوریا ǰoriya正是前文中提到的“着力牙”、“著力牙”的对音。该词在元代僧人所著《萨迦箴言》中亦有出现:“sayin morin ǰoriya bolurun sorɤaqsan-u šiltagha-bar”(由于将良马训成了ǰoriya)。蒙古谚语中还有这样的例子:“oroɤa ni oroɤa-bar ǰiruɤa ni ǰiruɤa-bar”,类似于汉语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语音历史变化的角度来看,可能有一个*ǰoriɤa> ǰoriya> ǰorā(ǰurā)的过程。而ǰoroo可能经历了 *ǰioriɤa> ǰiruɤa>ǰoroo。所以朮剌或住剌的准确对音应为ǰurā。现代蒙古语族诸语言中该词的口语读音几乎都为ǰoroo,只有和静地区方言仍为ǰorā,与古音相近。
从该词的含义来看,其行走方式为“对侧步”。一匹优良的朮剌马是要经过复杂的训练过程才能成就,并且该马本身就具备一定的素质,并非任何马匹皆能训练成功。即便是经过一番复杂训练已培养好的朮剌马,如果使用不当又会变回一匹普通马,最后功亏一篑,甚至“且与常马等不可得”。此外,撺行马虽行走迅速,利于骑乘,但不宜驮载重物和长时间奔跑,否则会“走死铺马”。从“对侧步”这种行走方式来看,其速度也不会特别快,至少不是仅以速度取胜,而是行走的“技术”至为关键。《老乞大》中记载的汉人与高丽人的一段对话也能说明这一问题。高丽人共有六匹马,汉人指其中的一匹马问:“…这个马也行的好?”高丽人回答:“可知有几歩慢窜,除了这个马,别个的都不甚好。”从这两句简短的对话可以看出,书中的汉人对马匹的情况非常熟悉,一眼就能从六匹马中发现优劣,并能猜到这匹马行走技术好。高丽人的回答果然不出所料,“可知有几步慢窜”是说这匹确实是会“窜行”的马。“慢窜”是说明窜行马也有速度快慢之别,也不排除高丽人有谦虚的成分。但关键在于这匹马是窜行马。可见当时一匹马是否能卖上好价钱主要在与行走的好坏有很大关系。
四、元代对“朮剌”马的使用和管理
有关窜行马与普通马之间的差异,元代文献中有间接的记载可供参考。党宝海已注意到《老乞大》中的相关记载。在一份关于马匹交易的契约中,估价一匹普通的骟马为中统钞5~7锭。而在后文中又提到“骑的呵,五十锭的好窜行马”。可见它们的价格几乎相差十倍,虽不能肯定这是当时确切的价格,但一匹上好的窜行马比普通马昂贵许多是不成问题的。
据文献记载,元廷在各驿站畜有此种马匹,其目的可能是专门提供给贵族或重要使臣利用的。但时有使臣殴打站赤人员,强行选拣窜行马的案件发生。元廷对此多次重申,使臣不得越级挑选蹿行马骑乘。《永乐大典·站赤》中记载:
元贞二年 月 日,钦奉圣旨:
通政院官人每奏:“‘站户每,不拣谁休隐藏者,属上都、大都两路站户根底,和雇和买不拣甚么差发休重并要者。差去的使臣,撺行马休拣骑者。站家草地每不拣谁休占了。[占了]来呵,回与者。’么道,薛禅皇帝圣旨有来。如今,属站的,站里差使趓避了,城子里官人每根底、各投下里[投入去的也]有,站家草地每百姓占了不曾[回]与来的也有。”么道,奏来。如今,站户每不拣谁[休]交影占者。大都、上都两路站户每根底,和雇和买休要者。但属站的草地每,不拣谁占了来呵,回与者。撺行马休拣骑者。道来。这般宣谕了呵,站户每影占的,大都、上都两路站户每根底和雇和买要的,属站底草地每不回付的,撺行马拣骑的人每,不[怕]那甚[么]?
么道,圣旨俺的。猴儿年正月初七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这是一通成宗时期(1296年1月7日)颁布的圣旨。从圣旨内容可以得知,在世祖忽必烈时期就有隐占站户,向上都、大都两路站户摊派各种差发,挑选窜行马,侵占站户草场等行为。为保护站户的权益,防止站户逃逸,保证驿站的正常秩序,世祖特降旨对上述违法行为予以禁止,但违反规定的使臣仍有存在。此次通政院官员向即位不久的成宗奏报,有属站的(即站户)逃离驿站,投靠了城子里的官员及各投下(即诸王、公主、勋臣),有人侵占了站户的草场,却拒绝返还。于是成宗再次降旨重申了世祖过去的规定。元代此类圣旨往往以重申前朝皇帝过去的圣旨的形式颁布,其目的可能是以前朝皇帝的威信遏制贵族或特权人物的违法行为,在圣旨结尾部分再加一句“不怕那什么?”(难道不怕吗?)来增加威慑力。尽管如此,收到的效果并不理想,违犯规定殴打站赤人员,挑选撺行马骑乘案件有增无减。《永乐大典·站赤》又载:
(延祐四年)九月,大都路良乡驿言:“自闰正月二十五日,涿州驿送到晋王位下来使锁秃等四人,又西番大师加瓦藏卜等七人到驿,各索走窜马匹,提领百户皆被鞭棰,越次选取窜马供给。二月一日,复有西番僧短木察罕不花八哈失等二十一人,起正马三十二匹,回马十匹,需求走窜马匹,棰挞站赤,恃威选马,无所控诉。窃照,本驿置于辇毂之下,南北冲要,供给浩繁,似此被害,何以堪命,乞禁治事。”省部照拟得:“国家设置驿传,所以通边情、备急务。近年以来,诸官府给驿繁数,站民匮乏,至于今岁尤甚。且大都南北六道站赤,比之各省,又重苦之,朝廷每加优恤。今此所陈,良可哀悯。若不严行禁约,诚恐逼临站户逃窜,废绝站赤,深为未便。”都省出榜诸站及下各路依上施行,仍咨行省一体禁治。
引文中的“走窜马”、“窜马”,也就是本文讨论的住剌马。与前引成宗年间的圣旨不同,此次良乡驿站的站官反映的内容非常具体。越次选取窜马,殴打站官的人主要有两部分人。一是晋王位下使臣,另一种人是西番僧人。此时在晋王之位的人是真金之子甘麻剌的长子也孙铁木儿(又译也孙帖木儿、也孙铁木而),即后来的泰定帝。从甘麻剌至也孙铁木儿两代晋王已长期为元廷镇守北边,手握重兵,自世祖时期就“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委付来。”晋王使臣的肆意妄为,自然因有晋王做靠山。忽必烈去世时元被册立为太子的真金已不在世,本来作为真金长子的甘麻剌是与其胞弟铁穆耳争夺皇位的最强大竞争对手,但在关键时刻提出“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并主动提出拥立铁穆耳,即位后的成宗对长兄甘麻剌的感激自不待言。后也孙铁木儿袭封晋王,又拥立武宗、仁宗、英宗三位皇帝。皇室对晋王家族的特权也是有默许的。西番僧人本身与皇室的关系密切,享有许多特权,这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赘言。由于以上的原因,朝廷一再颁布禁令都收效甚微也就无足奇怪了。最后无奈的元廷不得不采取妥协的办法,下令驿站禁止畜养窜行马。这再次说明,有元一代,以皇帝为代表的集权派和以晋王家族等各投下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存在,最终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一矛盾给元朝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以上所谈元代驿站中使用的朮剌(住剌)马是已经驯养成熟了的,可以放心给人使用的马。通过前文讨论,我们已了解驯养这些马匹是要一个复杂过程,并需有专人负责管理。元代众多的军队和庞大的驿站系统也会需要大量的朮剌马。那么在元代一定会有人在某地专门从事这一事情。据《元史》卷100《兵志三》“马政”条记载,元代有十四道牧地,其中提到“云内州拙里牙赤昌罕”、“拙里牙赤斡罗孙”、“乐亭地拙里牙赤、阿都赤、答剌赤迷里迷失”等,多次出现拙里牙赤一语,其中还有一处误为拙思牙赤,中华书局点校本已作出校正。拙里牙赤就是ǰoriyači的音译,即专门驯养朮剌马的人,昌罕、斡罗孙、迷里迷失等人就是其中的几个。 (本文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教研培训中心 讲师)
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四辑,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
责编:百川

- 上一篇: 黑龙|丝绸之路上的卫拉特人
- 下一篇: 喀喇沁蒙古文书法培训基地举办 蒙古文书法进校园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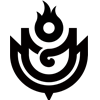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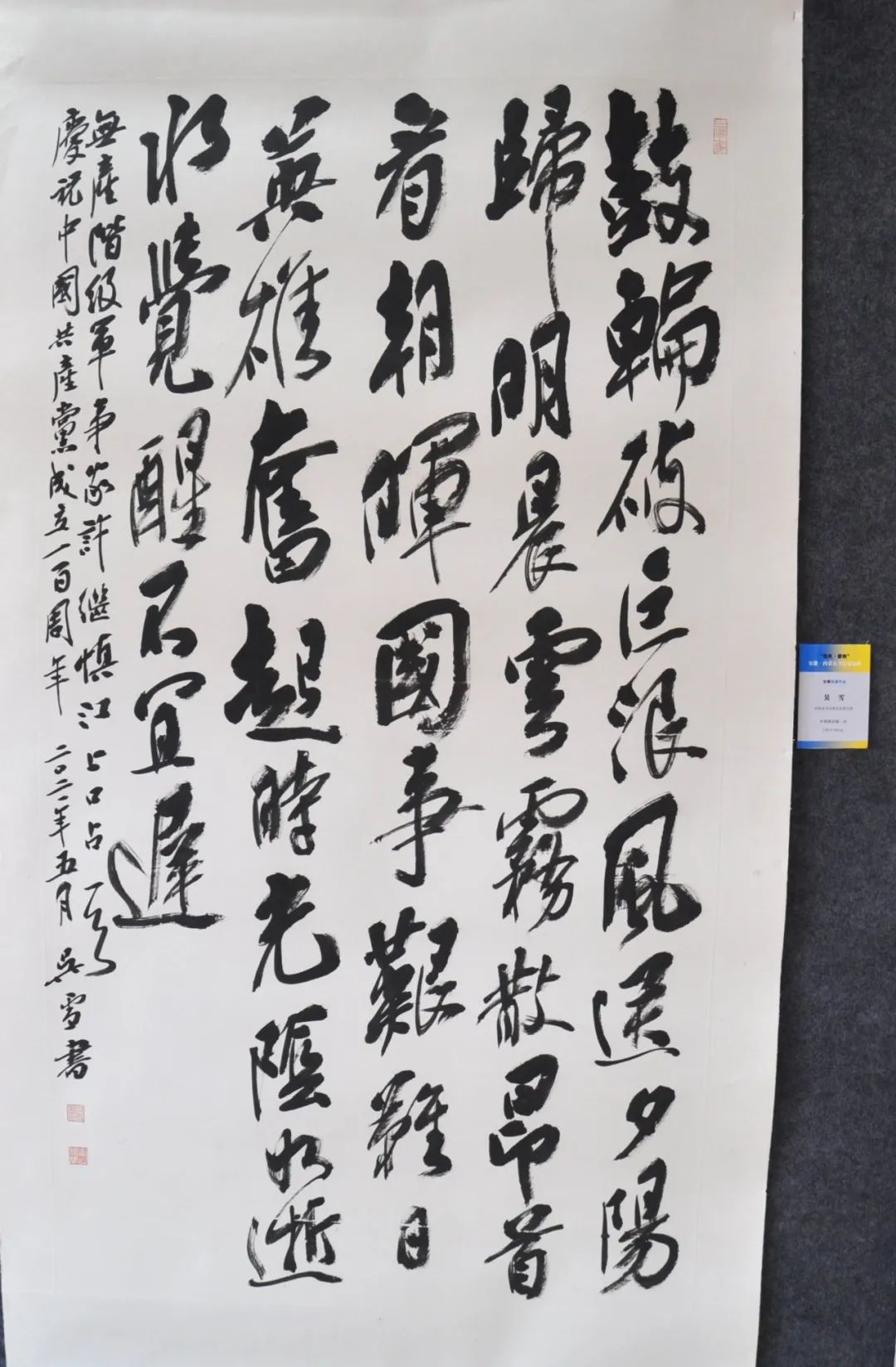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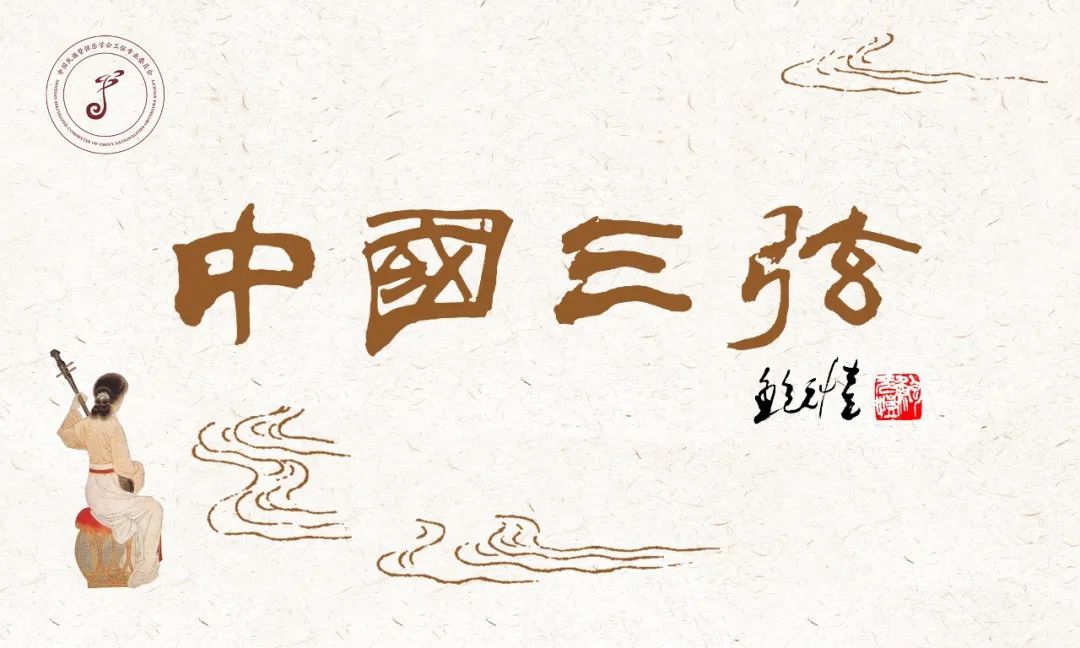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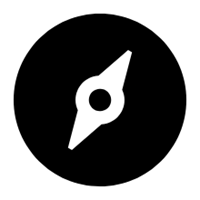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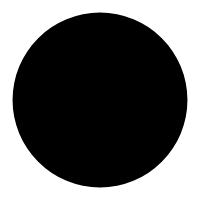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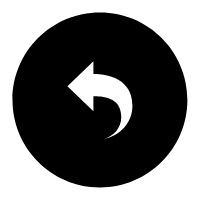
发表评论